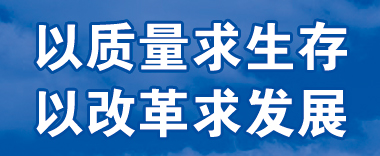我的爷爷,童年的酒
我的童年,泡在爷爷(我的二爷,父亲的养父)的酒里。那味道,醇香浓烈,让人心醉,让人流泪。爷爷的酒瓶空了,我的童年也一去不复返。今夜,月光如酒,缓缓流淌。满上一杯,入喉,又香又辣,味道和爷爷的酒一样,我的童年,又回来了。心中升腾一团火,燃烧许许多多往事,我的童年,又不见了。
爷爷爱喝酒,以他的酒量酒风,爷爷绝对配得上“酒仙”的称号。我的童年,和爷爷在一起的日子,温馨、甜蜜,充满了诗意。
父亲说过一个爷爷的往事,这也许就是爷爷喜欢喝酒的原因之一。重庆谈判之后,国民党穷兵黩武,一支国军部队路过家乡,补充兵员,爷爷被抓进兵营。部队开拔的头一天晚上,一个军官带着爷爷,找到村长,气势汹汹地说:“这个人有毛病,不适合行军打仗,不要了!”村长大眼看看爷爷,小眼瞅瞅军官,一脸纳闷:“老总,这个人都不要,你们是要金人还是银人?”也难怪村长疑惑不解,年轻时的爷爷,浓眉大眼,高高的个子,虎背熊腰,走起路来,虎虎生风,是村里人公认的百里挑一的好人材。后来才知道,爷爷处变不惊,急中生智,他想了一个好主意。爷爷听说负责训练新兵的军官爱喝酒,就投其所好,买了两瓶好酒,又塞给了他点儿钱……于是,就有了上述戏剧性的一幕。酒,改写了爷爷的人生轨迹。从此,爷爷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爷爷喜欢喝酒的另一个原因,是他和奶奶结婚多年,没有生育。爷爷闷闷不乐,借酒消愁。1942年,豫地大旱,又遇蝗灾。三爷和三奶奶(父亲的亲生父母)去山西逃荒。1947年,三爷回家,父亲已经三四岁了,大姑也一岁多了。爷爷见父亲长得唇红齿白,活泼可爱,满地乱跑,把父亲抱在怀里,喜欢得不得了,连声说:“看看这孩子,看看这孩子,给我吧。”爷爷和三爷商量,父亲过继给了爷爷。爷爷愁闷的心情云开了,雾散了,但他爱喝酒的惯性却刹不住车,驶向岁月深处。
爷爷的酒量很大。这个酒量大,不是说爷爷一顿能喝多少酒,而是指爷爷一天能喝多少酒。爷爷一天能喝多少酒?没算过,不知道。爷爷的一天从喝酒开始,以喝酒结束。早上,还没有起床,爷爷就抓起酒瓶,咕咚咕咚灌上几口,似乎只有这样,才会从梦中醒来。晚上,临睡前,爷爷又是几口下肚,似乎非得如此,才能解除他一天的劳累。我躺在爷爷脚儿头,满室酒香缭绕,我就像喝醉了一样,醺醺然,悄然入梦。
爷爷是闲也喝,忙也喝,喜也喝,愁也喝。天天如此,周而复始,月月如此,年复一年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密县老城东关有一个酒厂,零售散装白酒。每个月,爷爷都会让父亲给他买两塑料壶(五公斤容量)酒。跟着父亲进县城读书以后,给爷爷买酒,我拎着空壶去,父亲掂着满壶归,酒香飘一路。父亲的同事碰见了,就说:“刘师傅,又给你爹买酒啊。”父亲笑笑:“是啊,老爷子就好这一口。”若是跟着父亲回老家,我就提着酒壶,跑到爷爷面前:“爷,爷,给你的酒。”爷爷摸摸我的头:“好,好,刘狗儿回来了。”那酒壶,经过爷爷、父亲、我的抚摸,都有包浆了,温润如玉。酒壶即使是空的,也散发着浓浓的香味儿。
每个月两壶,二十斤的酒,够爷爷喝吗?怎么会呢?这也太对不起“酒仙”的称号了。这两壶酒喝完了,爷爷还经常去村里的供销社买酒。那个年代,我能记住的,只有伏牛白。有时候,爷爷会给我钱:“刘狗儿,去西头(供销社在村西),给我买瓶酒。”我乐得这样,一蹦一跳地就去了。因为剩下的零钱,我可以买糖买零食。为此,妹妹总说爷爷偏心眼儿。偏心眼儿就偏心眼儿吧,没办法,谁让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儿呢?即便如此,爷爷的酒,还是不够喝。没事儿,爷爷有办法。他让奶奶烧开水,兑到酒里面,爷爷喝他自己造的“假酒”。
爷爷的酒风很正。在我的记忆中,爷爷从来没有喝醉过,这可能与他化整为零的喝酒方式有关。爷爷不像有的人,一次喝一斤二斤,烂醉如泥,酗酒闹事,丑态百出。这种事儿,从来与爷爷不沾边儿。爷爷一次最多喝一瓶,尽管他能喝,很能喝。村里哪家办啥事儿,爷爷去上礼,总是带着我。乡亲们知道爷爷爱喝酒,就把一瓶酒放在爷爷面前。爷爷谢过主家,不与别人猜枚行令,独自风卷残云,酒足饭饱,起身走人,不管宴席是否结束。
老家院里,有棵香椿树。除夕夜,奶奶会让我抱着树,唱童谣:“椿椿你为王,你长粗来我长长,你长粗了使材料,我长高了穿衣裳。”我的个子总也不显长,香椿树倒是一个劲儿地往上蹿。过年时,奶奶再让我唱那首童谣,我心里就有些不情愿。每年春天,奶奶摘下香椿叶儿,洗净、晾干、撒盐、揉搓,封存。吃的时候,拌上小磨油儿、辣椒油儿、醋,油汪汪的,香气扑鼻。那是爷爷专属的好下酒菜,放在桌子的抽屉里。每到吃饭的时候,我就端着碗,一个劲儿地盯着香椿菜。爷爷哈哈一笑:“刘狗儿,来,来,吃香椿菜。香不香?”怎么能不香呢?爷爷吃一口菜,喝一口酒,眉头眼角儿满含笑意。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:爷爷喝的不是酒,是王母娘娘蟠桃宴上的玉液琼浆。
爷爷年轻时,走南闯北,行走江湖,见过许多人,经过许多事。所有的人和事,苦也好,甜也罢,都装在他的心中,泡在他的酒里。繁星满天的夏夜,在院子里铺上凉席,爷爷喝着酒,兴致高时,就会讲故事给我们听,给卧在他身边的小狗——阿黄听。爷爷讲书上的故事,讲戏里的故事,讲他亲身经历过的往事。父亲说的那个爷爷的故事,是“盗版”。爷爷讲的,才是原汁儿原味儿的正版。爷爷讲得声情并茂,眉飞色舞,听起来,别有一番趣味,惹得我们哈哈大笑。有的故事,经历时惊心动魄,爷爷讲起来,却是云淡风轻,无所谓喜,无所谓悲。讲到精彩的地方,阿黄也竖着耳朵,听得津津有味,仿佛在啃着一块儿大骨头一样。有的故事,听得满院寂静,无声无息。星星忘了眨眼睛,蛐蛐儿停止了鸣叫,阿黄也闭上眼,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只有爷爷苍老的声音飘荡在夜空,只有酒的香味儿在夜风中荡漾。听着听着,我困了,爷爷就摸摸我的头,拍拍阿黄的头:“都睡吧,日子长着呢,以后再讲。”于是,我回屋,阿黄进窝儿,各自安睡。
父亲带我去县城上学的那天,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,扭过脸,哭着喊“奶奶,爷爷……”奶奶颠着小脚,哭着喊我:“刘狗儿,刘狗儿……”爷爷坐在大门外的石头上,不说一句话,只是狠狠地猛喝他的酒。父亲把自行车蹬得飞快,不一会儿,就看不见奶奶的身影,听不见她的哭声了。远远地,风中飘来的酒香,伴随我一路,伴随我一生。
人生总是有许多没有实现的心愿。爷爷生前曾感慨地对我说:“刘狗儿,你姐要是个男孩儿,我都有重孙子了,也算是四世同堂了,你娶妻生子,我怕是看不到那一天了。”说这话时,姐姐已经结婚,大孩儿都两三岁了。我高中毕业时,八十二岁的爷爷喝完他人生的最后一瓶酒,饮尽岁月这杯酒,带着他的遗憾,离开了人间。
日子真地像爷爷说的那样,很长很长吗?有时候是,有时候不是。我觉得,爷爷去世这三十年,就像我和他在一起的一天一样,一晃而过。我和爷爷在一起的一天,就像他的酒一样,醇厚,绵长。酒是会燃烧的水,燃烧我的思念,灰烬如黑蝴蝶一样飞向遥远的夜空。前几天,喝酒,醉了。夜里梦见爷爷。爷爷喝着酒,笑着对我说:“刘狗儿,你和你爹一样,都是书呆子,也都是好样的,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吧。我那孙子媳妇贤惠勤劳,很能干。重孙女儿聪明漂亮,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。”从来没有喝醉过的爷爷,这次是真的醉了。醉了,醉了。醉翁之意不在酒,欧阳修在意的是山水,爷爷在意的是什么?
Copyright @ 2016-2021 zmjt.cn All Rights Reserved 制作单位:郑煤集团信息管理中心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》 豫B1-20060044 豫ICP备12008426号
地址:郑州市中原西路66号 电话:0371-87781116
全国互联网安全管理服务平台备案号: 豫公网安备 41010202002883号
豫公网安备 41010202002883号